《自焚藏人档案》于2013年9月由台湾雪域出版社出版,记录了2009年2月27日-2013年7月20日,境内120位自焚藏人、境外4位自焚藏人的档案,以及境内外7位试图自焚或自焚未成的藏人档案,以及2009年之前自焚的两位流亡藏人的档案。这之后,至2014年4月15日,境内外又有11位藏人自焚抗议,在此补充记录:
2013年8-12月,5起自焚(境内藏地4起,境外1起)第125位藏人自焚:2013年8月6日,僧人嘎玛俄顿嘉措在加德满都自焚牺牲![]() 嘎玛俄顿嘉措(ཀརྨ་ངེས་དོན་རྒྱ་མཚོ། Karma Nyedon Gyatso):
嘎玛俄顿嘉措(ཀརྨ་ངེས་དོན་རྒྱ་མཚོ། Karma Nyedon Gyatso):境内当雄(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羊八井镇)人,僧人,39岁。
2013年8月6日,拉萨传统节日“雪顿节”之日,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当地时间上午7时半,传出一位藏人僧侣在博拿佛塔转经道上点火自焚,当场牺牲的消息。
一位澳洲游客陈述目击盘腿而坐的嘎玛俄顿嘉措自焚情形:“我以为他点酥油灯时大腿不小心着火。然后我看见他往头上倒了瓶似乎是汽油的液体,火势蔓延开来。我没听到他发出声音。我开始呼喊求救。他蹲着,一脸扭曲可是却没喊叫。约2分钟后一路人拿着一桶水往他身上泼浇灭火势。另一位男子拿着灭火器出现。他的僧袍已烧成灰烬。”
约15分钟后尼泊尔警察抵达现场,用红布将自焚藏人遗体包裹带走。目前尚不得知尼泊尔当局将如何处理。
嘎玛俄顿嘉措于1974年出生在拉萨当雄县羊八井镇,俗名为丹巴竹杰,流亡前为羊八井寺僧人。他的父亲名叫嘉央扎西,母亲名叫吾坚。他于2012年1月30日流亡抵达位于尼泊尔加德满都的西藏难民接待站,曾去过印度,后返尼泊尔。
第126位藏人自焚:2013年9月28日,牧民西琼在阿坝县各莫乡自焚牺牲西琼(ཞི་ཆུང་། Shichung):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阿坝县各莫乡)人,牧民,41岁。
2013年9月28日下午约4点半,牧民西琼从当地正在举行的名为“缅顿”的法会上返回家中,而后在自家门前将自身点燃,喊着口号向公路跑去,随即倒地牺牲。
僧俗民众将西琼遗体送回他家,当局派出上百军警进行威胁,要求交出西琼遗体。在村里老人恳劝下,民众们只能眼看着西琼遗体被军警抢走,法会也只好提前结束。之后,西琼的遗体被当局擅自火化,骨灰被当局强迫撒入河中。
自焚牺牲的西琼遗下妻子和一对儿女,妻子名叫瓦罗,39岁;女儿名叫才波,18岁;儿子名叫平措,14岁。西琼除放牧务农外,平时还兼做裁缝,为乡亲缝制藏装。
而在当地举行“缅顿”法会时,当局诸多官员与军警到现场进行警告与监视。当时西琼曾对朋友說:“这些汉人不会让我们安心,我真的需要在他们面前实施自焚。”这应该视为西琼留下的遗言。第二天中午,西琼在尊者达赖喇嘛法相前供奉了一盏酥油灯,继而点火自焚。
西琼自焚牺牲后,当地的各莫寺和赛格寺及民众受到当局严格管制。
第127位藏人自焚:2013年11月11日,僧人才让杰在班玛县自焚牺牲才让杰(ཚེ་རིང་་རྒྱལ། Tsering Gyal):安多果洛(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人,觉囊派阿什琼寺僧人,20岁。
2013年11月11日下午5点左右,僧人才让杰在班玛县城丁字路口的“八瓣莲花”像前呼喊“嘉瓦仁波切千诺”(意为尊者达赖喇嘛,请护念我),点火自焚,重伤,被军警灭火后带往班玛县人民医院,随后在转往省会西宁医院的途中,才让杰牺牲。
才让杰在牺牲前,给两名陪同他的亲属留下遗言:“我今天是为了境内外藏人团聚而自焚,一定要搞好藏人内部的团结,保护好西藏的语言、文字和传统习俗,这是我唯一的愿望。若能这样,境内外藏人定能团聚”。
才让杰出生于班玛县江日堂乡的牧民家庭,父亲名叫西彭,母亲名叫仁卓,家有八个兄妹,他的舅舅朱古强曲白是阿什琼寺的住持。
才让杰自焚的时间,正值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在北京召开之际。
才让杰是班玛县自焚的第二位藏人。2012年12月3日,班玛县班纳合寺僧人、29岁的洛桑格登在班玛县莲花街三岔路口点火自焚,双手合十,呼喊“藏人们请团结!”、“不要内斗!”,当场牺牲。之后,当地多名藏人因为从军警手中抢回洛桑格登遗体而遭当局严惩,被判刑1年半至10年不等。
而才让杰自焚牺牲后,当地僧俗藏人多达17人陆续被当局拘捕,包括阿什琼寺高僧图旺仁波切、纠察师布达嘉、纠察师格勒及其弟次拉杰等人。
才让杰家乡的江日堂寺堪布益西宁布遭当局通缉,在逃难中。当地女教师央措因手机微信上存有堪布益西宁布发来的才让杰照片被开除公职,还遭毒打住院。
第128位藏人自焚:2013年12月3日,牧民贡却才旦在阿坝县麦尔玛乡自焚牺牲贡却才旦(དཀོན་མཆོག་ཚེ་བརྟན། Konchok Tseten):安多玛曲(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人,后入赘到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麦尔玛乡),牧民,30岁。
2013年12月3日下午5点左右,牧民贡却才旦在阿坝县麦尔玛乡政府前点火自焚,呼喊“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让尊者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境内外藏人早日团聚”,双手合十,倒下后被当地干部扑灭火焰,随后被军警和警察强行带走,多名藏人因阻拦被拘捕,包括贡却才旦的妻子及其几名亲属。
贡却才旦在被军警带往阿坝州首府马尔康县的途中不幸身亡。他的遗体被中共当局擅自火化,虽然将其骨灰交给了贡却才旦的一名亲属,却没有说明关于火化的情况。
贡却才旦出生于甘南州玛曲县齐哈玛乡吉勒合村的牧民家庭,父亲名叫桑阔,母亲名叫奥嘎。他入赘到阿坝县麦尔玛乡成家,妻子名叫南囊,现28岁,两人有两个儿子:4岁的恰多杰,3岁的华泽杰。
贡却才旦因带头参与2012年1月23日在阿坝县麦尔玛乡发生的上百名藏人示威游行活动,被中共当局通缉,但一直未能被抓捕。
第129位藏人自焚:2013年12月19日,僧人次成嘉措在夏河县阿木去乎镇自焚牺牲次成嘉措(ཚུལ་ཁྲིམས་རྒྱ་མཚོ།Tsultrim Gyatso):安多拉卜让(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阿木去乎镇)人,阿木去乎寺僧人,42岁。
2013年12月19日下午2点45分,僧人次成嘉措在阿木去乎镇的街上点火自焚,当场牺牲。当地僧俗藏人用黄绸将他的遗体包裹,送回阿木去乎寺,约400多名僧侣为次成嘉措举行了超度祈福法会。但军警闯入阿木去乎寺抢走次成嘉措的遗体,并在夏河县拉卜楞镇火葬场强行火化。当局还张贴“四个坚决不准”的藏汉文通告:“一、不准聚集、围观自焚事件。二、不准僧人为自焚者超度、诵经。三、不准吊唁慰问自焚者家属。四、不准私自处理自焚者尸体。”
次成嘉措在自焚前亲笔写下遗书,题为:
雪域斗士次成嘉措为了藏人的团结与福祉而自焚——金子般的眼泪
唉!眼泪,心口疼痛。
亲爱的哥哥,你能听到吗?你能看到吗?六百万藏人的苦难向谁诉说?黑汉人暴虐的监狱,夺走了我们黄金白银般的宝库,使百姓们处于苦难中,想起这,不禁流泪。
将我宝贵的身体燃烧,为了尊者达赖喇嘛返回故土,为了班禅喇嘛获得释放,为了六百万藏人的福祉,我将身体献供于烈火。以此祈愿消除三界众生的苦难,证得菩提之道。
佛、法、僧三宝,请保佑无助的人们。雪域同胞们要团结,不要被奸诈小人受骗。
——雪域斗士次成嘉措。
次成嘉措出生于安多桑曲阿木去乎尼玛龙部落(今夏河县阿木去乎镇尼玛龙村)的牧民家庭,父亲名叫旦正扎西(已故),母亲名叫拉姆吉,家中还有才贝、觉巴、桑杰卓玛三个兄妹。次成嘉措17岁时进入阿木去乎寺,是一位深怀慈悲、修学有成的合格僧人。
次成嘉措是第5位自焚的阿木去乎镇人,是第16位自焚的夏河县藏人。
2014年2-4月,6起自焚(境内藏地6起)第130位藏人自焚:2014年2月5日,牧民彭毛三智在泽库多禾茂乡自焚牺牲彭毛三智(འཕགས་མོ་བསམ་འགྲུབ། Phagmo Samdub,又写帕莫桑珠):安多泽库(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多禾茂乡牧民、在家密宗修行者,27岁。
2014年2月5日晚约21时半,牧民彭毛三智在多禾茂乡第二完小(又称万青宁寄宿制完小)附近点火自焚,迅即赶至的警察将重伤的彭毛三智强行带往泽库县,当局立即严密控制通讯,严防自焚信息外传,并部署大批公安和武警,对泽库县城、自焚之地多禾茂乡及邻近县区采取了严密的戒备措施。有消息指他在自焚现场已经牺牲。
彭毛三智是多禾茂乡塔士乎村牧民,及在家密宗修行者,有妻子和年幼的儿子与女儿。其母名叫珠姆。
彭毛三智自焚后,当局拘捕了他的弟弟、僧人嘉措,以及华多夫妇、白玛、才旦加等藏人。
之前,仅在泽库县多禾茂乡已发生4起自焚抗议事件,即:2012年11月17日自焚牺牲的牧民桑德才让;2012年11月23日自焚牺牲的牧民达政;2012年11月25日自焚牺牲的尼师桑杰卓玛;2012年12月9日自焚牺牲的女中学生班钦吉。而最新发生的彭毛三智的自焚,即多禾茂乡第5起自焚抗议事件。
彭毛三智是2014年第一位自焚藏人。
第131位藏人自焚:2014年2月13日,洗车店主洛桑多杰在阿坝县自焚牺牲洛桑多杰(བློ་བཟང་རྡོ་རྗེ། Lobsang Dorjee):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贾洛乡人,曾为格尔登寺僧人,自焚前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经营洗车店,25岁。
2014年2月13日下午约18时半,洛桑多杰在阿坝县洽唐街(被当地民众称为“英雄街”)呼喊抗议口号,双手合十,点火自焚,部署在阿坝县城的大量军警迅即赶至现场,扑灭洛桑多杰身上的火焰之后将他强行带走,随即阿坝县戒备森严。三天后,即16日,洛桑多杰在阿坝州州府马尔康县的州医院牺牲,他的家人要求当局交还遗体被拒绝,只收到骨灰。当地很多民众为他去寺院点灯祈福。
洛桑多杰出生于阿坝县贾洛乡的牧民家庭,父亲名为才巴,母亲名为娜梅吉,有四个子女:姐姐达措,妹妹梅梅,弟弟扎西,洛桑多杰为老二,尚未结婚。
洛桑多杰曾为格尔登寺僧人,还俗后与母亲和弟弟在相邻不远的达日县经营洗车店。数日前,洛桑多杰回到阿坝县家里,朝拜寺院,参加法会。昨日自焚前,他还去格尔登寺观看金刚法舞。
迄今,仅属阿坝县贾洛乡籍的自焚藏人就有11位,即:2012年1月6日自焚牺牲的牧民次成,2012年2月11日自焚牺牲的尼姑丹真曲宗,2012年2月13日自焚后生死不明的僧人洛桑嘉措,2012年3月4日自焚牺牲的牧女仁钦,2012年3月5日自焚牺牲的牧民多杰,2012年3月28日自焚牺牲的僧人洛桑西绕,2012年8月6日自焚牺牲的僧人洛桑次成,2012年8月27日自焚牺牲的僧人洛桑格桑,2012年8月27日自焚牺牲的牧民旦木曲,2013年2月3日自焚牺牲的僧人洛桑朗杰,以及,2014年2月13日自焚后生死不明的洗车店店主洛桑多杰。
第132位藏人自焚:2014年3月16日,僧人久美旦真在泽库县自焚牺牲久美旦真(འཇིགས་མེད་བསྟན་འཛིན། Jigme Tenzin):安多泽库(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僧人,29岁。
3月16日早上7点,久美旦真在泽库县夏德寺外自焚,重伤。夏德寺僧人将他抬到寺院,为随即牺牲的他举行了超度祈福法会。当局立即封锁了该地区的通讯,并从夏德寺抓捕了14名僧人,其中11人至今被拘留。在拘押期间僧人皆遭毒打。久美旦真的两个兄弟于18日遭拘押,23日获释。久美旦真的父亲呼吁当局不要惩罚夏德寺,却于3月22日被拘捕,至今下落不明。
目前夏德寺有大量军警进驻,所有僧人被“软禁”,参加为期100天的“法制教育”。
久美旦真出生于泽库县夏德日乡牧民家庭,父亲名叫拉杰嘉,母亲名叫央廓。久美旦真为夏德寺僧人,并在安多地区著名大寺隆务寺(位于热贡即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学佛多年。
第133位藏人自焚:2014年3月16日,僧人洛桑华旦在阿坝县自焚牺牲洛桑华旦(བློ་བཟང་དཔལ་ལྡན། Lobsang Palden):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3岁。
3月16日,是2008年安多阿坝抗议民众被当局军警枪杀六周年纪念日。自此,3月16日被藏人称为“阿坝屠杀日”。始于2009年2月27日的第一起自焚,即格尔登寺僧人扎白正是因为纪念遇难者一周年的祈祷法会被取消而自焚。之后,2011年、2012年、2013年的3月16日,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彭措、洛桑次成、洛桑妥美相继自焚牺牲,以表达对中共镇压阿坝及全藏的抗议。
2014年3月16日上午11点半,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华旦正是在西藏自焚抗议运动的第一人——扎白自焚之处点火的,也即阿坝县洽唐街。因为有十多位藏人在这条街上自焚,这里已被当地藏人称为“英雄街”,而传遍全藏地。伤势严重的洛桑华旦当即被军警带走,五天后牺牲在医院。
洛桑华旦出生在阿坝县麦尔玛乡三大队(阿谢仓)的牧民家庭,父亲已故,母亲名为南科,继父名为西热,有兄弟姊妹多人,并有弟弟也是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华旦自小出家,一直在格尔登寺学习佛法。他在自焚前留下给母亲、兄弟姊妹及老师、同修的遗书,主要内容是感恩母亲抚育,永远要做利他的善事,民族之间团结,特别要与汉人邻居团结,只有双方互利才能共存。
遗书内容如下:
“想要对父母、兄弟姐妹们说的是:民族间相互团结,诚心相待是正确的。心怀妒恨招致失败,诚心相待会成功是毋庸置疑的。同样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三思而行,不要愚昧行事是极为重要的。
“如果是学生,要做到学业有成;如果是父母,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如果是商人,要做到双方有利。不论是农民还是牧民,要孝敬父母。
“对全世界,特别是对汉人邻居要团结,只有相互团结有爱心,才可以将我们的想法向对方说明,也可以有所作为,不是吗?哦!我要向你们说的是,要时常把有利他人和有利自己区分来开,要常求有利别人,不求有利自己,因为幸福的根源是有利他人及团结一致。
“愿阿妈、祖母、姨姨、舅舅、姐夫以及我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及所有与我有关的亲人,以及,付出心血教育我的老师,我的同学们事事顺利,心想事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利他。
“我的阿妈啦!您用慈爱养育了我们,我们是在您的血汗中逐渐成长,我们在您的怀抱里得到无尽的快乐,您给予我们太多太多,让我们顺顺利利,没有任何困难,一切只因您的慈悲。感恩我的母亲!一切是您给的,如果要一一详述,永远也没法说完,所以就说这么多吧!
“以上一定有很多错别字,我向你们表示抱歉。(华旦,或雄鹰智华,或素食者,或哈哈哈短腿敬上)”
第134位藏人自焚:2014年3月29日,尼师卓玛在巴塘县自焚卓玛(སྒྲོལ་མ།Dolma):康巴塘(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人,尼师,31岁。
3月29日下午3时多,尼师卓玛在巴塘县被改名为“康宁寺”的曲德贡巴的转经路上点火自焚,在场的藏人信众立即扑灭火焰,并将烧伤的尼师卓玛送往当地县医院。医院立即被军警严密封锁,当地通讯曾被阻断,但据消息,尼师卓玛“目前暂无生命危险”。而当时与她一起转经的三位尼师,巳被警方带走,尚无消息。
尼师卓玛出生于巴塘西松贡乡(在金沙江对岸,现已划入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芒康县)的农民家庭,父亲名叫尼玛,母亲名叫旺姆。其家族名为东拉卡,是巴塘境内的大户人家,巴塘大寺曲德贡巴(被改名为“康宁寺”)的三位转世仁波切以叔侄辈份出生在其家族中,有多位前辈在1950年代反抗中共的战斗中牺牲或入狱。
尼师卓玛焚之前住日登寺,自焚之前在日登寺磕等身长头已有数月。
而尼师卓玛自焚的地点,正是3月30日早晨去世的藏人共产党人、革命家平措汪杰先生的家乡——藏东康区的巴塘县。这是在巴塘县发生的第一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
第135位藏人自焚:2014年4月15日,农民赤勒朗加在道孚县自焚牺牲赤勒朗加(འཕྲིན་ལས་རྣམ་རྒྱལ། Tinley Namgyal):康道坞(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人,农民,32岁。
4月15日中午12时多,赤勒朗加在道孚县孔色乡自焚抗议,当场牺牲。
当地僧俗藏人闻讯赶到自焚现场,将赤勒朗加的遗体抬往孔色乡的宁玛寺院各它寺,举行了祈福超度法会。之后,赤勒朗加的家人将他的遗体送回家中,17日深夜火葬。
赤勒朗加是孔色乡格勒村农民,父亲名叫堆罗,已经去世,母亲名叫白拉,他在家中三个子女中排行最小,尚无结婚。
赤勒朗加在自焚前给友人和家人留下遗言:“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困难,根本没有自由。”“藏人没有自由可言,连骑摩托车到县城购物都受到阻拦”。“如果自焚的话,对西藏整体利益有多大作用?对获得自由有多大帮助?”
赤勒朗加自焚牺牲后,他的生前照片及自焚现场照片迅速被传出,藏人们还在照片下用藏文写道:“在道孚有一位名叫赤勒朗加的同胞,为了藏民族的政教燃烧了自己的身体,是民族的英雄,我们表示沉痛哀悼。”
道孚县是康区敏感地区,2008年以来发生过群体抗议、祝福尊者达赖喇嘛诞辰集会、五次自焚抗议以及不过“洛萨”(藏历新年)、“罢耕”、“吉度呢颇”等不合作事件,一直被当局严防与管控。赤勒朗加自焚牺牲后,他的家人陆续遭到当局的传唤和恐吓,日琼等多位藏人被拘捕。
迄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已有5位藏人自焚抗议,包括僧人、尼姑、流亡者和农民,即:2011年8月15日自焚牺牲的道孚县灵雀寺僧人次旺诺布;2011年11月3日自焚牺牲的道孚县铜佛山觉姆庙尼师班丹曲措;2012年3月26日自焚牺牲的原籍道孚县、流亡印度的学生江白益西;2013年6月11日自焚牺牲的道孚县巴秀扎嘎寺尼师旺钦卓玛;2014年4月15日自焚牺牲的道孚县孔色乡格勒村农民赤勒朗加。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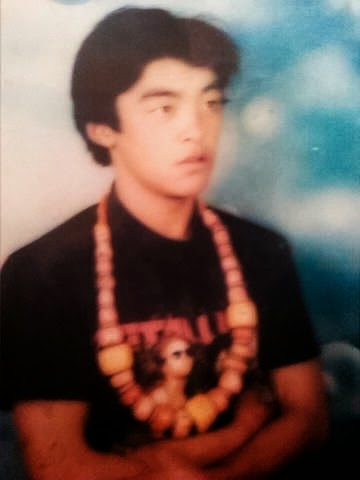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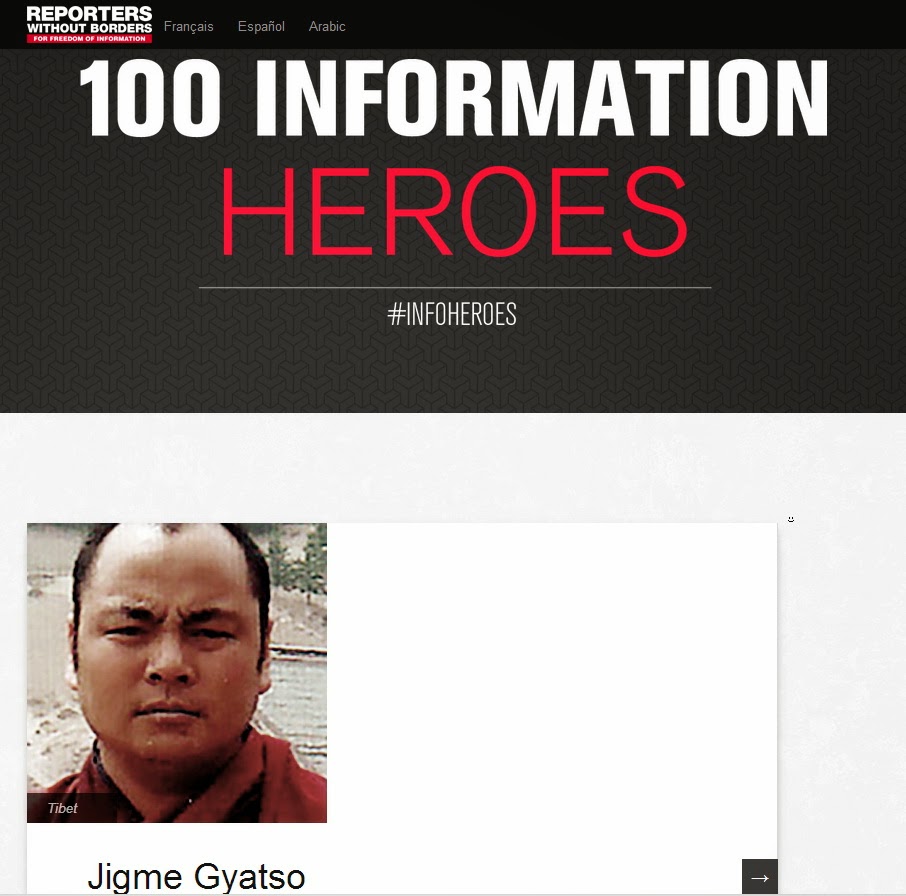.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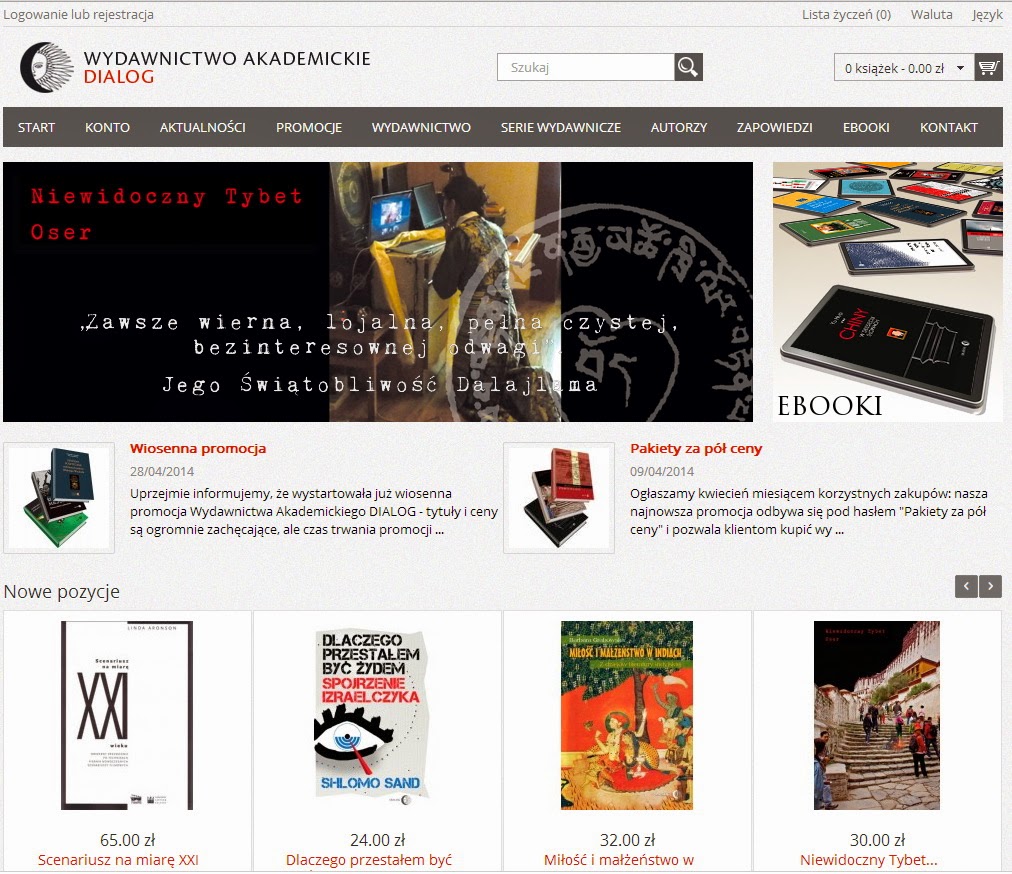.jpg)









.jpg)









